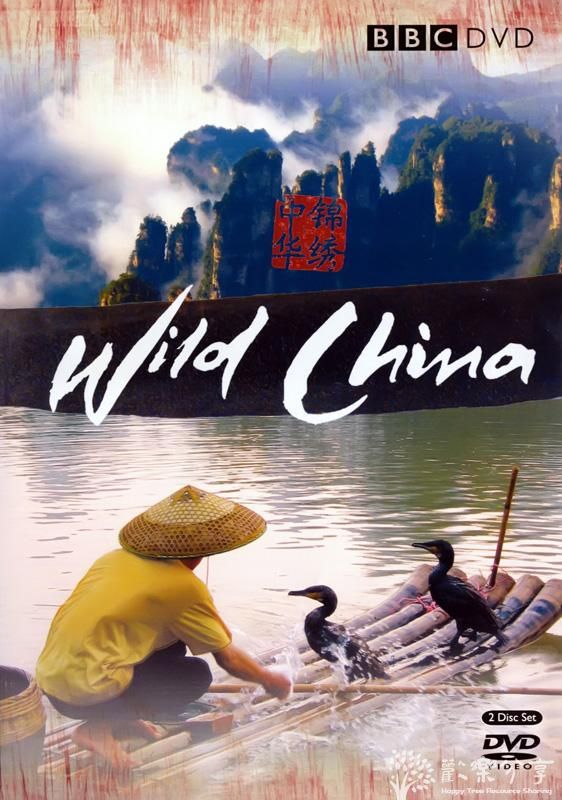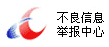本文选自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97级研究生刘勇宏的毕业论文《用光线书写——维托里奥.斯托拉罗电影摄影艺术研究》第三部分:“用光线参与叙事和表意的电影摄影理念”。指导老师:张会军、穆德远。
刘勇宏,电影摄影师,先后参与拍摄了《北京的风很大》《海鲜》《盲井》(银熊奖)《唐诗》《芒种》等多部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中国独立电影,同时还为当代最具活力的第六代电影导演和年轻的新锐导演掌镜拍摄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江城夏日》《蒙娜丽莎》《牛郎织女》《租妻》《乡兮》等多部艺术电影,确立了自己独特鲜明的影像风格。
“对我而言,摄影真的就代表着‘以光线书写’。它在某种意义上表达我内心的想法。我试着以我的感觉、我的结构、我的文化背景来表达真正的我。试着透过光线来叙述电影的故事,试着创作出和故事平行的叙述方式,因此透过光影和色彩,观众能够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感觉、了解到故事在说什么。”

维托里奥·斯托拉罗(左)与贝托鲁奇
“用光线参与叙事和表意”是斯托拉罗摄影艺术的最基本理念之一,这在他的许多作品里都得到鲜明而充分的体现。他认为电影摄影是在胶片上“用光写作”,是“以光线书写的文学”,电影摄影师是运用光影、色调、色彩,并调和了他个人的经验、感性、智慧和情感来创作的作家。
“以光线书写”的核心是用光线创作的影像“讲述”电影的故事,表现时空、情绪、人物性格、主题、节奏或其他无法言传的东西。
之所以确立“以光线参与叙事和表意”的摄影理念,首先是因为他对光线有自己完整的哲学认识:“光是一种最重要的东西,他给你一种世界的观念,它造就你并改变你,如果你出生在瑞士或列宁格勒,在白夜中生活几个月,看到永无止境的黄昏、充满阴影的世界,那你会大大地发展起一种同你出生在非洲完全不同的感觉,在那里全都是光。光会改变我们的身体,改变皮肤的颜色和血压,影响眼睛,甚至会决定我们理解世界的方法。光,它是力和能量。”

在他看来,光就是能源,人类不仅仅是由这种能源产生的,而且靠这种能源存在,虽然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意识到这一点,但它始终推动着世界,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一种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决定着一个种族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着一个人的视觉和心理的经验。影像的形成、复制和呈现也取决于光,它是光(能量)的印记,创造摄影影像的关键是光的结构和组织,它传递着影片的信息、形象、气氛、情绪、态度和意义。
确立“以光线参与叙事和表意”的摄影理念还与他对摄影在电影中的美学和材料特性的认识有关。在他看来,摄影光线本身虽然是一种能源,但你很难靠能源来传达感觉,必须将它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影像。光线会被物体或人阻挡,经由某种镜片纪录在底片上,然后冲印出来。这就像作家的纸笔或画家的画布一样,因此,摄影就是“以光线书写”。如果改变了一部影片的光的基调,那么就改变整部影片给人的感受,也会影响影片的情节。他说:
“电影摄影是一系列不同的视觉形象,不同的画面,即运动、变化着的光叙述,我每次仔细考虑一部影片究竟该怎样拍的时候,完全像写作的构思一样,考虑全片的光线的发展和变化。”
在摄影创作中,斯托拉罗用光创作出和故事平行的叙述方式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我认为拍摄一部片子,可以说是在解决明与暗、冷调与暖调、蓝色与橙色或者其他对比色调之间的各种矛盾。必须使人感觉到活力,感觉到变化或者运动,使人感觉到时间正过去,白天变成黑夜,黑夜又变成早晨,生命变成了死亡。拍摄一部影片很像是在纪录一次旅行,同时按照最合适这部特定影片和它所包含的思想的方式去用光。”
时空是电影叙事的基本载体,在斯托拉罗看来,摄影光线是电影叙事和表意的视觉化语言,是作为一个整体有机的结构表达电影时空的组成、变化和运动的,这个整体结构的组成要素有光线的形态、质感、方向、强度、色温、影调等等,它们的复合、组织和构成呈现出电影的时空运动,让观众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流逝、倒流、断裂和重新聚合,同时表达出电影的时空特征、氛围、情绪、感受、象征和意义。

这部影片是1987年中意合拍、贝尔托鲁奇导演的史诗性的电影,该片在1989年获得9项奥斯卡大奖,其中包括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摄影奖。该片打破了传统单一的线性叙事时空结构,采用了一种倒叙式的、套层式的时空结构,设计了两条并行发展的叙事时空系统:组织时空和插入时空,前者是影片时空结构的线索,后者是溥仪回忆的主观心理时空。组织时空的顺序为:东北抚顺(1950年-1959年)-北京(1959年-1967年);插入时空的顺序为:宫中(1908年-1927年)-天津(1927年-1934年)-满洲国(1934年-1945年)。
组织时空的光线设计基本上以自然光为依据,光比大,色调以冷调(蓝、绿)为主,气氛以日景为主,光线运动少,影调反差大,带有自然主义用光倾向;插入时空的光线设计以戏剧化用光为依据,光比小,色调以暖调(红、黄)为主,光线跳跃,影调黯淡,带有表现化用光的倾向。插入时空建立在组织时空的叙事逻辑基础上,两个时空系统不是分离的、无法辨别的,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不仅仅靠情节、细节、回忆和心理的契机建立,而主要靠摄影光线的特征、运动和节奏,场景的气氛和画面的影调的衔接和暗示建立的。
影片《末代皇帝》的导演贝尔托鲁奇说:“影片的主要思想是表现一个人在他的记忆中经历一番旅行,其间他不时重新思考他的人生。”

我们从分析可以看出这两个交错的叙事时空系统的光线特征的差异、对比和反差,而这种差异、对比和反差正是影片的整体光线设计立意和风格所在,也正是该片“用光线写作”的视觉语言,它出色地完成了参与叙事的任务,并在视觉上形成一种张力,表现出现实和记忆(主观)、自由和囚禁、潜意识和知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承载着多重的象征和隐喻。
在影片的结尾,当插入时空的叙事完成,溥仪的回忆结束,插入时空与组织时空融合,先前两个时空构成的光线对比和反差逐渐减弱,当影片的叙事只剩下组织时空的时候,摄影光线逐渐变得写实,完全以自然光的形态为主,色彩由原先的饱和恢复正常,影调的反差也适中,而叙事的主要内容是溥仪获得了自由,结束了漫长的回忆之旅,治愈了心理伤害,成为正常人。

从光线对时空的表意上分析,斯托拉罗认为在影片《末代皇帝》中,光代表知识,光线投射到人物身上产生阴影,象征着人潜意识的挖掘。他谈到影片《末代皇帝》的光线整体构思的时候说:
“中国的皇帝生活在特定的界限――城墙之内,总处屋顶、阳伞的阴影下,所以我们为影片确立了一种半阴影的基调。而光,则体现出一种自由精神。光,对于总被乌黑在阴影里的小皇帝溥仪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生理需要,而且意味着自由、解放。随着小皇帝的成长,对社会的不断认识,他不断超越外界对他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光线处理上慢慢加入了自然光的成分。”
斯托拉罗认为在影片中光象征着知觉的一部分,阴影象征着潜意识的一部分。在紫禁城里的阶段,溥仪在精神上一直是与外界隔绝的,他几乎始终处在成人、围墙、柱子、屋檐的阴影里,这阴影其实是时空压抑的隐喻。当私人教师庄士顿进入皇宫,给溥仪上课,溥仪不断获得知识,便不断获得光线,去挣脱时空的囚困。在不断获得对自我逐渐认识的过程中,象征潜意识的阴影范围也在扩大。因此,他在满洲国时,阴影部分战胜光的部分,溥仪完全被阴影笼罩,气氛主要以阴天和昼夜交界的傍晚为主;而在抚顺监狱里被改造时,光与阴影不再对立,而是趋于融合,影调也变得明快,意味着人物在自我分析和接受自我的心理运动过程中,对自我与潜意识进行着知识性的探索。最后,溥仪到花园工作,在这个自由、开放的空间里,光与阴影的对立趋于平衡。

我接受一部影片时,总是努力听取各种意见,总是努力拍出导演要求的那种样式或者风格。什么古典的、写实的用光方法我都不在乎。你一旦发现一种适合那部影片的格调,你就马上会这样拍一场戏。

人物形象是电影叙事的主体,电影人物形象不同于文学的人物形象,他是活动的视觉化的形象,除了演员的表演和服、化、道造型以外,摄影光线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着关键作用。这一点也是斯托拉罗的摄影理念表现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他看来,人物形象的创造离不开摄影光线对角色的塑造,摄影光线不仅应该可以刻画出人物的气质和性格,还应该呈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冲突,而这正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内在依据和动力。
电影中的人物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何用光线塑造电影叙事中运动变化的人物形象是斯托拉罗感兴趣的领域,具体来说就是人物造型光的整体设计,这里涉及叙事、情节、时空、环境、气氛和角色心理等诸多因素,即需要统一,也需要变化。
在斯托拉罗看来,人物光线设计不应有什么模式的束缚,只要符合导演的要求和影片整体的视觉基调,在局部处理上,古典的、写实的、戏剧的、或其他的什么用光方法都可以,重要的是与叙事和情节切合。
“这是一部反映两种文明社会矛盾的影片,表现了一种文明在另一种文明中的冲突和矛盾。科茨上校强烈地反对这种文明的冲突,他力图摆脱、取消自己带来的文明的阴暗面,而想极力表达出纯真的新的事实。”
在整体光线设计上,他采用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光——一种是傍晚夕阳西下时柔和的自然光,一种是用美国先进工业社会所拥有的电子设备制造出人工光来表达这种冲突。


他对科茨上校的光线处理也力图表现出这种冲突。按叙事结构的设计,科茨上校虽然是影片的主角,寻找他并杀死他是整个故事的悬念所在,但他在整个影片的前3/4都不出现,有关科茨上校的生涯和思想演变历程都是通过其他人的转述一点点交代的,即使这样,导演还是在视觉上通过一些黑白照片的特写,对人物做了多次细节描绘,在处理这些有关科茨上校的视觉信息上,斯托拉罗并未放弃摄影光线对人物的塑造。

第一次出现是在日景,照片是一身戎装的科茨上校的正面像,人物造型光是侧逆光,他的脸一半处在阴影里,戏剧化的条形从照片上划过,消色的照片与色彩浓郁的环境形成反差,叙事交代的内容是有关他的卓著战功和独特的处世风格,照片中的光景对立暗示着人物的内心柔和冲突;照片第二次出现是在傍晚和夜里,在黑暗里,上尉借助手电筒翻看科茨上校童年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彩色的正面像照片,人物造型光是散射光,照片上童年的科茨一脸稚气,手电筒形成的微弱的局部光(自然光照明)与黑夜弥漫的环境暗示着一种潜在的危机和混乱;果然,当科茨上校第三次在黑白照片上出现的时候,完全是戏剧式的用光,他背对着镜头,身子处在逆光当中,几乎是剪影的影调效果,光影形成强烈的反差,叙事交代的内容是他脱离了指挥,组建自己的部队和防区,试图用极端的暴力消除自己代表的文明的阴暗面,这种光线处理方式暗示在他内心的两种意识的冲突和对立中,阴暗面已经完全控制了他,同时为他最后出场时的用光形式作铺垫;第四次,上尉把他的照片撕碎,放入河里,科茨上校的影像完全破碎,暗示他已割断了与过去的所有联系。

通过分析,我们看到,人物虽然是在照片上作为细节出现,但每一次的出现都有与叙事内容和人物塑造有关的光线形态、气氛、影调、色彩和用光形式等光线构成元素的变化,这些变化让人无法直接看到科茨上校的音容相貌,形成神秘、诡异、悬念的心理效果,在表意上隐晦但准确地呈现出人物的鲜明的气质和性格,以及战争和现实对人物的精神异化过程。
最终,科茨上校在极具戏剧化的光线设计下的出场:他的室内如同洞穴一般,类似夕阳一样的、橙色的侧逆光打亮他的头部,在画面上形成月牙型的局部光斑,他的脸和身体完全处在黑暗中,画面在暗调处理,光影形成强烈反差。

“白兰度演的角色代表文明的黑暗面,代表潜意识或者来自黑暗面的真理。他不可能像两个正常人坐着聊天一样,正常出场。他必须是一个偶像。黑色是像巫术一般的黑色,你可以用暗色背景造成一种图案和风格,而这是只有用黑色才能表现出来的。拍摄前我在脑子里想象过这个场面,在想象中白兰度一直处在阴影或者黑暗的一边。”
如果不是前面照片的铺垫,他出场时的造型光是无法让人接受的,虽然那些视觉信息看似无足轻重,但对人物光处理的整体把握却非常重要。

另外,任何形式的圆形一直是斯托拉罗在摄影画面上设计图案喜爱使用的母题式的图形,在影片《蜘蛛的策略》《同流者》和《巴黎最后的探戈》的画面中出现的灯都是圆的,他个人认为这是一种象征,意味着两个一半的事件组合在一起,意味着平衡与和谐。科茨上校光头上月牙型的光斑恰恰是圆形的断裂,这在观众心理上暗示了人物内心中两种力量的剧烈冲突与对抗。
与此对应,斯托拉罗对上尉的造型光也作了整体的设计,影片虽然是通过上尉的视点展示他所目睹的残酷的现实,但实际也是追溯科茨的遭遇和精神历程。在寻找过程中,上尉的价值判断被逐渐颠覆,最后他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完全被自己文明的黑暗面控制,当他杀死科茨的时候他也已成为另外一个科茨。

在开始,上尉的造型光还主要以自然光(农业文明的象征)的形态为主,当他在经历种种屠杀和死亡洗礼之后,他内心中的黑暗面在逐渐扩大,这在视觉上的表现为他越来越多地受到人工光(工业文明的象征)的照射;当他见到科茨的时候,他的造型光已经完全与基本科茨一样:侧逆光,大的影调反差,箭头型的逆光光斑。最后一场戏,他要去杀科茨的时候,斯托拉罗在他的造型光中是加入强烈的、闪动的人工光,使他的右边脸的影像不断在瞬间由低密度状态变成高密度状态,这种戏剧性极强的光线设计,真实表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和混乱。

总的来说,影片《现代启示录》的人物造型光是与整体的光线风格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斯托拉罗对主要人物的造型光进行了细致处理,较好地完成了造型、叙事和表意任务,同时形成鲜明的用光风格。
在摄影创作中,斯托拉罗用光线创作出和故事平行的叙述方式还体现在许多方面,可以说“用光线书写”的摄影理念是他创作的摄影哲学。他在理论上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的摄影观念体系。在实践中,他一直进行不懈实验和总结,创作出一批出色的、体现出这种摄影理念的作品。他作品和理论对当代的电影摄影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资源均来自用户分享和网络收集,资源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研究使用,禁止商业用途,如果损害了您的权利,请联系网站客服,我们尽快处理。 【免费的东西不长久,支持作者才有动力开发】